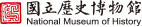首頁 / 您好,我是XX 或(OO媽媽)
首頁 / 您好,我是XX 或(OO媽媽)妳的Line稱呼是什麼呢?
Line是現代人最常用的聯繫方式之一,它的稱呼就像一個人的名片,反映自我身分認同。而Line稱呼的變化,也可以識別出一個人身分的變化。某些女性為了公事需要,會在姓名前後加上公司名稱或職稱。某些女性,選擇進入婚姻,在鄰舍親朋的人情往來間,稱呼逐漸變成他人口中的「X太太」。部份有寶寶的女性,等到北鼻上幼稚園,或入學的那一天——新生報到時,笑咪咪的老師把每位家長加入班上的群組,以便緊急狀況需要聯繫,方便起見,媽媽們往往會在名字後加上:「OO的媽媽」。
臺灣早期女性與傳統父權家庭結構,以及農業社會經濟架構緊緊相繫。女性的價值,往往視她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,或是她為「家庭」付出了多少決定。社會期待女性不但出得廳堂、進得廚房,還能悉心照顧子女。日殖時期,臺灣女性在學校修習的實用性課程,是為了操持家務而準備。日殖時期至1960、70年代,女性的角色以家庭為重心,以一種溫婉的「好太太」形象,或是能在農忙之餘,能照顧好家裡所有孩童的「神力媽媽」的形象存在。
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社會學教授亞莉.霍希爾德(Arlie Hochschild)在1989年提出「第二輪班」(The Second Shift)的概念。簡而言之,在傳統社會分工中,承擔大部分家務的是女性。時代變遷,當女性得到良好教育,走入職場成為常態,社會的傳統框架並未隨之調整,仍希望女性繼續操持家務,因而造成職業女性下班後,回家必須照顧家庭、完成家務;家務也成了她下班後的「第二份工作」。
史博館館藏中有一張特別的照片,畫面是凌亂的,有別於一般攝影作品精心設計的美感。這是攝影家蔡惠風1960年代拍攝的《家居生活》。照片中的母親,穿著上班時的外套、襯衫和窄裙,坐在榻榻米上,幾個孩子依偎在她身邊,旁邊則是杯盤狼藉的矮几。
這幀照片似乎透露著職業婦女上完一天班後,回家仍要整理家務、照料孩子的辛勞與忙亂。臺灣女性普遍受過高等教育,在職場上也能發揮所長,地位看起來大幅提升。然而,根據2017年人力資源公司統計,近8成臺灣女性仍認為難以兼顧工作與家務;時至今日,工作家庭兩頭燒的狀況仍是女性必須面對的難題。根據2021年行政院性別平等處發布的《性別圖像》:「女性平均每日無酬照顧時間為其配偶或同居伴侶的3倍。」今日,職業婦女工作強度不亞於男性,在家庭中如能共同分擔家務,或鼓勵男性留職停薪在家育嬰,讓兩性都能在工作與生活之間取得平衡,或許更適合現代社會的家庭結構。
清廷統治下的臺灣,女性從事的職業多為技藝、勞力取向,如:刺繡、編 織蓆帽、茶葉加工等等。日殖時期,日本政府引入工業,資本家們開設工廠,女性勞工的比例也不停增長,如:紡織女工、女性接線生等等,雖然往往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狀況,但工廠內供食宿等福利,仍吸引許多臺灣女性前往就職。另一方面,女性在家中從事加工補貼家用也從未斷絕,且和臺灣不同地區的特產息息相關。如:1920年代張清言拍攝妻子在「羅山信用組合」學習編製大甲蓆帽的景象,便反映了當時大甲編織業的興盛;而另一幅妻子烘製龍眼乾的樣貌,也反映了1920年代晚期,女性在家幫忙從事物產加工的狀況。
此外,也有從事服務業的女性,如喫茶店的女服務生「女給」、百貨中的女性銷售員、以及客運、火車上的車掌小姐等等,她們往往以光鮮亮麗的「毛斷」(日殖時代用詞,意為modern摩登)女子形象示人。
隨時間推移,臺灣由農業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,政府獎勵投資,設置加工出口區,女性在工廠勞動,在產線上辛勤工作;有些女性為了兼顧家務,在家代工,「客廳即工廠」的景象風行一時,這些女性也是臺灣經濟成長不可或缺的一份子,有些一肩扛起整個家庭的經濟重擔。
此外,外型亮麗姣好,形象光鮮、談吐合宜的車掌小姐,還曾是臺灣女性心目中最嚮往的行業之一。1930年代,臺灣已出現車掌小姐。1959年,公路局推出金馬號長途對號快車。1970年代以降,又引進金龍號、中興號及國光號,在這些車輛上,都有隨車的車掌小姐。她們的工作主要是遞送茶水、毛巾與書報、介紹沿途站別等,近似於今日的遊覽車服務小姐。由於車掌小姐可在外接觸人群,增廣見聞,又配有美觀的制服與船形帽;在公家機關服務,薪資相對穩定,甚至還可請領配給;還由當時的中國小姐訓練儀態、應對禮節,基於以上誘因,成為競爭最為激烈的行業之一。但車掌小姐一旦進入婚姻或懷孕,就得離職。
本館館藏的攝影作品大多為男性攝影師所攝,女性是他們鏡頭捕捉的題材,取景上也多為男性視角出發。但女性攝影師的成就亦不遑多讓。1930-40年代,曾受教於前輩攝影師彭瑞麟的施巧,以及前往日本東洋寫真學校學習攝影的連金枝、陳麗鴻等,是臺灣早期的女攝影師。其中1921年出生的陳麗鴻,在當時男性主導的攝影圈中,毅然前往日本學習攝影,歸國後以細膩的視角與靈活的商業嗅覺,在攝影界一枝獨秀,良好的人緣與管理能力也讓她擔任四屆臺北照相公會理事長,以及永久榮譽理事長。除此之外,臺灣首位系列性的女性報導攝影家王信,也率先於1970年代自日本將報導攝影引入華人攝影界,她認為報導攝影須具備客觀記錄性和主觀的指導性,更必須實現社會改革的目標。